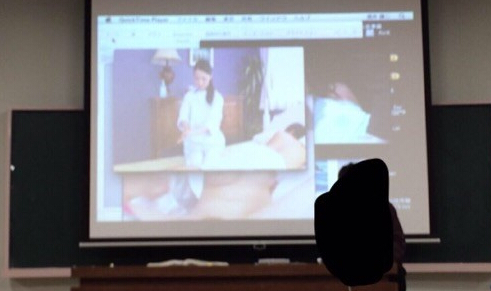日本女导演拍300部色情电影:从未迎合男性!你信吗?
 这个行业里30年来只有我一个女人。所谓的现场磨练,也就是经历过作为一个女人可能受到的各种羞辱。
这个行业里30年来只有我一个女人。所谓的现场磨练,也就是经历过作为一个女人可能受到的各种羞辱。
导演浜野佐知导演浜野佐知
为实现导演梦只能从拍色情电影起步
问:您为什么要进入粉红映画摄制行业?
浜野佐知:1968年,20岁的我高中毕业后到东京开始寻找当导演的路。那时日本也没有国立的电影学校,不能上学学习,本打算在电影公司找份工作,边工作边学习电影。当时在日本的几大电影公司控制了所有日本电影的制作与发行,但招工的条件是大学毕业的男性,作为女性绝对进不去。那有没有其他办法呢?最后我发现只能从做粉红电影导演,也就是色情电影导演开始积累拍摄经验。
问:那么您为什么一定要做电影导演呢?还要付出先做色情导演的代价。
浜野佐知:高中时我开始喜欢看电影,欧洲那边又兴起了艺术电影的浪潮。这种新浪潮的电影中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对我影响很大,都是比较自立的女性形象。
可是当时日本的电影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所以电影中的形象包括母亲妻子各种女性的形象,都是以男性为主,千篇一律。涉及到性描写时,牵涉到的女性又多半是娼妇或者被抛弃的离异女性。我觉得这是因为都是男导演拍的缘故。
如果能做电影导演就能拍摄出真实的女性形象。
男导演拍的色情电影只聚焦女人下半身
问:根据资料显示,粉红映画出现在1962年,由日本独立制片商制作的低成本的以描写男女性爱为内容的色情片。拍摄的作品被称为300万电影,因为每部片子的制作费为300万日元,每年大概要制作300部电影。您所看到的粉红映画是什么样的内容?能简单说说主题和视角吗?
浜野佐知:刚开始接触粉红映画的时候我几乎被吓住了。什么样的呢?男性拍的粉红电影都以男人为中心,女人的性都是为了男人,一切以男性的欲望为主,把女人的身体物化,剥夺女性人格,只聚焦女人下半身的电影。比如说所有的影片都有关于强奸的描写,把表现强奸视为理所当然。而且情节中被强暴的女性还竟然爱上侵犯她的男性。
我想女人并不是为了迎合男人,为了张开大腿才存在的。女人也有自身的性和欲。
我希望拍摄只有女人才懂得,只有女人才能创作的作品,这就是我下决心要成为一名粉红映画导演的初衷。
问:当时除您以为还有专业拍摄这一类影片的女导演吗?
浜野佐知:当时没有,此后30余年都只有我一个女导演,没有其他人。粉红映画和其他电影不同,用不着场记也无须布置场景和房间,也基本没有女性工作人员。
问:粉红映画在电影界的地位如何?
浜野佐知:当时的地位还是比较低,不是主流,也不能进入普通院线放映,只能在专门的放映厅上映。它和AV完全不一样,比如学生们只能偷偷的去那种店里面借AV看。
第一部作品就是描述女学生自主选择性爱的故事
问:您在拍摄前会对电影剧本进行修改吗?您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样内容?
浜野佐知:最开始不是自己写的剧本。男导演作品中的女人是为了等待男人挑选而存在的。女人由男人来挑选,女人永远是被选择的。在性行为的时候,也是男性主动,女性被动。
到我33岁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为独立的女性导演后,虽然所有的脚本都是山崎先生来写,但电影的风格和性描写都已经有别于以往的粉红映画作品了,电影中表现的女性形象都是自发的主动的想要发生性行为的女性形象。
我一开始就想挑战男性为主的社会。
我的首部作品是想挑战男性的性幻想,他们觉得如果女人被强奸也是有高潮的。这部作品描写的是17岁女孩自己选择男人自己选择性行为方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自立长大成人的故事。
这部作品被很多男导演批判,因为是女生主动做爱,他们认为没有这样的现实。
问:70年代的时候,日本一家大的电影公司日活濒临倒闭时制定了新的策略,开始制作浪漫情色电影。粉红映画和这种电影有什么不同?
浜野佐知:大家常有把浪漫情色片和粉红映画混为一谈的倾向,但日活制作的这一类电影和粉红映画不同。日活公司是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它的预算跟粉红电影不一样,大概是10倍以上。粉红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电影而存在,从思想上和技术上也是完全不一样。
日活公司有3000万的预算,但没有办法自由选择想拍的电影主题。粉红电影因为其独立性则正好相反。
色情电影行业30年只有我一个女导演
问:电影评论界对您导演的粉红映画有何评价?
浜野佐知:我的电影是想让女性看的,希望女性看了之后能够开心。他们最开始就批判我的作品,不过男性观众喜欢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我在片子里常常挖苦男人,大约评价不会太好吧。
这个行业里30年来只有我一个女人。即便在整个日本,从现场磨练出来的女导演也许也只有我一个人。所谓的现场磨练,也就是经历过作为一个女人可能受到的各种羞辱。
拍电影被男人性骚扰 只好抱着刀睡觉
问:作为粉红映画的女导演,肯定会与男演员和其他剧组工作人接触,在交往过中有没有让您为难或难堪的事情?
浜野佐知:我22岁时做导演,演员、剧组工作人员都是比我年纪大的男性,怎么会不受欺负呢?即使当了导演也免不了。他们会开一些下流玩笑,用今天的话来说毫无疑问是性骚扰。但因为这种事情就闹起来的话,在粉红映画圈中,我一个女人就干不下去了。
比如某天晚上喝醉的组里的男人突然爬到我床边想和我上床,有时候我都抱着刀子睡觉,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别的男生想看我跑步时候胸部颤动的情景。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无所谓,因为当时我一定要当导演,这是更重要的。
比如在野外山间拍外景,哪里来的厕所啊,真的会愚蠢到和男人并排站着小便。
我最被困扰的不是性骚扰或者权力的骚扰,而是自己有生理的那个身体。
拍外景为规避生理期长期服用避孕药
问:您是指拍外景时遇到生理期吗?
浜野佐知:对啊,怎么克服每月一次的生理问题呢?拍外景对女人来说实在是很不方便,因为女人被赋予生儿育女的身体,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至少在60年代后期,月经棉条护垫还很不普及,不是随时随地可以买到的。即便是有的也还存在厕所和时间问题,有厕所又没时间,有时间又没有时间。拍外景有时忙起来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碰上这种时候想停拍是不行的。
没办法我当时只好吃避孕药来调节生理期。但当时日本没有被认可的避孕药,我就去一些地下医院买那种不正规的药,对身体副作用特别大,脸就变得非常肿。之后会有其他的男性说,就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不需要女性导演。
什么性骚扰啊,受欺负啊,挥一挥刀子什么的都可以挡回去。可是对自己的身体,我却毫无办法。到底是女人的身体,一直影响着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克服了这些种种困难。
不觉得羞耻 从未拍过迎合男性的作品
问:粉红电影的受众大多是男性,是否会为了迎合他们做些让步?拍娱乐男性的色情电影是不是对女性的一种侮辱?
浜野佐知:我制作粉红电影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自己想要就去做的这种独立女性形象,我从来没有拍过一部电影是为了迎合男性的。
女权主义者从批评到接受 最后还为一部剧情片募捐
问:粉红映画肯定会受到很多女权主义者批评,那么遭到批评时,您如何承受呢?
浜野佐知:我不觉得羞耻,因为我一直是在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为了在电影中还女性的本来面貌而单枪匹马努力了30年,光靠动嘴是没有用的。
之前的女权主义者把粉红映画中的女性色情内容作为批判对象,但是近年出现的女权主义者看待这些是一种艺术。她们对敢于表现女性的性爱这些场景是一种赞扬的态度。
当年我接受电影《尾崎翠》的制作时,是以松本为首的日本女权主义者们支持了我,全国有一万两千多位女性为我募捐。这也是我和女权主义最初的邂逅。那是在1998年。如果总结我所走过的历程,或许这就是我和女权主义的渊源。
只是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跟商业、女权都无关
问:这么多年您一直要表达女性自主自由的主张,那是不是意味着您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浜野佐知:我自己其实没想过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我非常开心别人认为我是女权主义者。虽然自己也没有实际的这么认为。我在人生中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拍这些作品来表达女性主义,我是非常开心的。在日本有种说法是色情电影把性商品化。我拍这些电影也一直被批判,被女权主义者被批判。
但我做这些最重要的目的是在电影里表达女生的性由女生自己来掌握。
我想拍的是我自己想拍的,跟商业无关,跟女权主义也无关。要说我是女权主义者的话,因为我也在不断地与父权体制及男性社会做斗争,而且也是一个人的斗争,既没有组织,也不是权威。
实际上我只是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问:当年您拍色情电影时家人怎么看待这份工作?
浜野佐知:因为我拍的这种粉红电影倾注了自己非常多的努力。家人看到我这样努力之后是非常的支持。我自发的非常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家人当然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欢电影,想做剧情片导演,通过电影表达自己想说的东西。有了这个信念才能做到现在。
剧情片《百合祭》关注老年女性的性爱
问:2001年,您拍的描述老年女性的性爱故事的剧情片《百合祭》在国外获得了几个大奖,评价很高,在几十个国家巡映。这次来中国参加国际女性影展,您也带来了这部电影。为什么您会关注老年女性这个群体?
浜野佐知:拍了30年色青电影之后才开始拍上剧情片。其中一部就是《百合祭》。我想描述的很多,尤其在描写高龄女性的情欲时,我试图从正面去表现一种复杂交错的情欲。我希望得到一种效果,就是观众在笑声中看这部电影,笑过之后还能思考一下老年女性在日本社会所受到的待遇。
在日本,拍摄老年女人性爱是被禁止的,有关闭经之后的女性做爱类型的电影也不受欢迎。而且大部分男性超过40岁之后可能也不会勃起,在日本社会也被认为是不能做爱的。
日本社会塑造的传统而理想的老龄妇女形象对世人影响极大。比如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中那种装束整洁举止安详,与上了年纪的干瘪老头闲坐品茶的可爱的小老太太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
在日本社会里,女人如果闭了经,就似乎应该作为老人老老实实呆着。过去人的寿命差不多只有50年,女人月经没了也差不多要死了,因此不存在老龄情欲的问题。现在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有87岁。
女人过了50岁有更多选择 更应好好享受性爱
问:您在拍摄《百合祭》时多大岁数?是否也和您自身经历有关?
我拍摄《百合祭》时正好50岁左右,自己的身体内有何变化?性欲消失了吗?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仍然充满了爱的愿望。闭经了又怎样?什么女性激素减退,其实也没有变。没了月经,倒是更自由了,做爱也不会有孩子了,应该更放得开了才对。
日本女人如果过了50岁还找男人就被看成是老妖精,就要被人疏远。我就是要把她们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我要告诉她们过了50岁,正好可以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可以有性,有爱,有情欲。不能把剩下的37年闭着眼说成是余生。如果闭经真的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那么其后的新阶段里人生变得更加充实,应该去重新考虑情欲和性爱的问题。
国外频频获奖 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可能只是启蒙
问:这部电影在日本放映后影响如何?
浜野佐知:《百合祭》是14年前拍的,不过直到现在,日本社会还是不太关注老年女性的性爱。而且在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放映后,2005年才在日本上映。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看过,但是看过的人其实有变化。我是想告诉大家,实际上上了年纪这件事情不只有坏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
很多高龄女性看完电影后都是非常开心地走出来。有个83岁的女观众后来告诉我,她找到一个男朋友,他们每周去一次情人旅馆。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只是一个启蒙。
更改原作结尾是想表达老年女人可以追求想要的生活
问:《百合祭》原著作者是男性吗?原著结尾和电影一样吗?
浜野佐知:原著作者是女性,但原著结尾和电影不完全一样。这部电影描述了一个老年男人入住一所全是老年女人居住的公寓后,和其中几个女性发生关系的故事。原作中当男主角完全暴露后,就以派对结束了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电影就没意义了。
原作偏重于男性主义,而我偏重于女性主义,所以结尾我改成两个女性变成了情侣关系,女主角之前没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因为在美国有这样的人,上了年纪之后才发现自己是同性恋。
问:《百合祭》的旁白是一个过世了的女性角色。您怎么会想到让已经死去的人做旁白呢?
浜野佐知:我是以一个死去的老太太的视角拍的,相信大家能感觉到,死去的人和女主角关系比较好,这是一个比较暗的线。这是原作中没有的,但是我依然觉得死者和女主角之间有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最后女主变成了同性恋者,这是一个为情节开展而埋下的伏笔。可以想象,如果做旁白的角色还活着,就她们的关系发展来看,很可能走上同性恋之路。
问:《百合祭》结尾处公寓中的几个女人知道真相后仍旧相安无事,也有人说您有厌男情结。
浜野佐知:我不是不喜欢男人,而是不喜欢日本社会的男性至上主义。
电影结尾处几个女人知道真相后仍旧相安无事,是想表达女性的解放,只是通过男人来享受性爱。
最后两个女人在一起也是因为开始了其他谈恋爱的方式。如台词所说,上了年纪之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和性别无关,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性生活。
电影中出现了两次百合花开的声音,也是想表达女性享受性爱后发现了自己的新生。
问:这次影展您带来四部剧情片,您对观影的中国观众有什么样的印象?
浜野佐知:中国观众是完全没有顾虑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日本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可能会看一下周围,看周围的人有没有笑,他才会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但是我到中国来发现中国的观众想笑的时候就笑想说的时候就说,我对这一点非常的高兴。
浜野佐知
日本导演,生于1948年,理想是从女人的角度拍摄女人的电影,反对电影对女人的刻板印象。她从东京开始自己的电影之路,当年电影业仍是男性主导的行业,不愿意任用女性做导演。最终她决定先从拍摄情色电影起步,积累拍摄电影的经验。此后一段时间她曾在独立制片公司作导演助理,1971年首次以导演身份登场。1984年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旦旦舍,1998年拍摄了独立电影《第七官界的彷徨 寻找尾崎翠》,这部电影展现了几乎被遗忘的女作家尾琦翠的生活和工作,赢得了Hayashi Amari奖。同年,她开始着手拍摄桃谷方子描写老年女性性需求的小说《百合祭》,并于2001年将其搬上了银幕。2005年出版了名为《女が映画を作る!》(女人拍电影!)的书,2006年拍摄《蟋蟀女孩》,2011年拍摄《芳子与百合》,2015年拍摄《变性记》